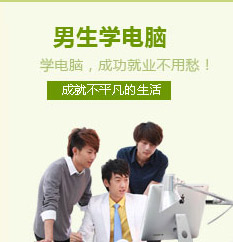潤物無聲育愛心,鼓勵引導促興趣
轉載自:人民政協報社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庭教育經歷。那些在時間悵惘中浮現的往事,那些在閑聊中憶起的點滴,都是我們人生旅程中留下的印記,或深或淡,對我們產生了潛意識的影響,匯聚而成我們的性情或品格。
我兒時因為父母都在工作,更多是我奶奶帶大的。我妹妹出生后,奶奶又從鄉下來幫我父母,所以她也陪伴了我的少年時期。每當我憶起奶奶時,她對我的寵愛、鼓勵、提醒和保護,是我童年時期無法抹去的溫情。也許理性的教育認為,祖母對孫子的寵愛對孩子的成長會有負面的影響。但我個人的體會是,祖父母輩對孫輩天然流露的愛,是孩子愛的體驗的重要源泉,甚至對于那些父母過于忙碌或嚴格的孩子而言,還是愛的體驗的主要來源(當然,也有可能,祖父母是嚴格的,而父母特別是母親是提供愛的主要源泉)。很難設想,一個童年時沒有多少愛的體驗的孩子,能夠成長為一個身心健康的人,只要這樣的寵愛不走向毫無原則的溺愛,有來自家庭其他長輩起作用的平衡。所以,我時常給退休的老師開玩笑說,盡管去愛你們的孫兒和外孫,讓父母去管教他們。我的體會是,從愛的體驗中,才會滋養出孩子善良的心地。同樣很難想象,一個少兒時期沒有多少愛的體驗的孩子,會成為一個有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人,無論其受到的教育多么嚴格和理性,多么符合抽象的仁義道德。
我奶奶是文盲。我念小學一年級時,她才用患白內障的眼睛,使勁盯著我課本上的第一課,學會了認出“毛主席萬歲”這幾個字,她那認真勁兒,她那由衷的喜悅,給了我莫大的鼓勵。我曾經蒙她,老師批改作業本時用紅筆打的鉤,都是好。當她拿起我的作業本,湊到半瞎的眼前,映著窗口的光線,看到滿篇的鉤,露出發自內心的滿意笑容時,我感到多少有些自責的欣慰。我的基本價值觀中的“善良”和“與人為善”,是在她講的老故事和往事中、她與鄰居的交往中、他對我的小伙伴們一視同仁的態度中、我挨父親打時她擋在我身前甚至躲閃不及也挨上幾下的保護中,滋養的。善良源于愛,狹義地愛家人,廣義地愛他人、愛家鄉、愛祖國,這樣的愛心和同情心,我相信自己是在祖母一言一行、言行一致的熏陶下形成的。
對于大多數孩子來說,他們的第一個世界是家庭。所以,家人的陪伴很重要。現在的孩子,課業負擔很重,“不要輸在起跑線上”的觀念,更把競爭提前到幼兒少兒時期,“別人家的孩子”也總是有形無形地敲擊著父母的神經。現在的父母,工作壓力也很大,無論是生計還是事業,總之沒有多少時間陪伴孩子,而把孩子的成長完全寄托于學校,只是接到家長通知“氣急敗壞”時灌輸一些空洞乏力的口號式觀念,揮舞一下功利性的訓誡。各方面的壓力和單維度的評價都過早地把孩子推入孤獨和競爭的境地,使心智發育初期的孩子心理扭曲,無法自然正常成長,造成心理問題,抑制天然好奇,身心健康受到損害。這不僅對于獨生子女家庭如此,將來對于雙子女家庭也如此,只是程度可能有些差異。這既不利于孩子的成長,也不利于社會的健康,更不利于國家的未來。
家人特別是父母的陪伴之所以重要,因為不僅孩子心智的發育、品格的形成是需要在潤物無聲的持續熏陶中才能成長,孩子的好奇和興趣也是需要在持續的互動和鼓勵下才能發展的。這是天然的需要,就像孩子反復要求母親念一個故事、父親做一個游戲,從而在滿足中心田得以無形地滋潤一樣。孩子是需要玩伴的,在玩耍中產生興趣,在玩耍中學會交往,在玩耍中得到激勵,在玩耍中形成基本的價值觀。而父母應該是孩子的第一玩伴。
回想兒時,父親時不時買幾條金魚放在臉盆里,后來又允許我先在砂鍋罐、后在水缸里養小魚小蝦,夏天傍晚帶我去捉蜻蜓,冬天教我做風箏、一起放風箏,這都與自己成年后葆有一些好奇心,以至每到一個學習階段都換一個專業領域,不無關系。父親做人做事的誠懇實在,對弱者的同情幫助,對不公的人與事的態度,母親對小說的興趣和樂于助人的忙活,都無形中影響了我。再想想自己,在兒子的成長中很少陪伴他,不是以成人世界的搞笑價值觀逗弄他,讓他云里霧里,不知認真何在,就是脾氣上來,以學業為由,粗暴銷毀他偷偷買的漫畫雜志、否決已經承諾的動漫時間權力,甚至威脅清除他養的螞蟻,實在追悔莫及。稍有安慰的是,兒子高中時,自己答應幫他住校期間伺候螞蟻的那一刻,他那感激的眼神和同謀般的表情。
在與孩子的陪伴互動中,鼓勵和引導至關重要。記得“文革”后恢復高考時,我剛上初二,幾乎沒有學到什么東西。父親著急,就開始親自輔導我,與我一起做平面幾何題。一次父親表揚我的解題方法比他的好,給了我極大的激勵,以至于一段時間家里熄燈后,我躺在床上,腦子里都是幾何題中的圖形,不斷添加各種輔助線或搜索相似的三角形,也讓我養成了可以不用看著資料文稿討論問題的習慣和能力,就像下默棋一樣。如果要說我對自己的兒子有什么看得見的影響,我能夠想到的就是,有段時間,我們一家人一開車出游,車上就會反復播放約翰·列儂、保羅·麥卡特勒、鮑勃·迪蘭、約翰·丹佛等歌手的歌曲,結果他喜歡上了他們的歌。2016年當瑞典文學院宣布鮑勃·迪蘭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兒子第一時間在QQ上告訴我:老爸,厲害了……我感受到了我們父子共同的興奮和喜悅。對孩子的最大鼓勵是父母對其興趣的認可。兒子喜歡觀察螞蟻,就像我小時候喜歡觀察魚一樣。對他的這個興趣,我一直有矛盾的心理,表現出矛盾的態度。直到有一天他給我講了他崇拜的哈佛大學科學家、“社會生物學之父”愛德華·威爾遜后,我才知道對螞蟻的興趣可以造就如此杰出的科學家。我由此閱讀了一系列威爾遜的書,他關于科學與人文融合的觀點和思想給了我很大啟發。我想,我對威爾遜教授的興趣也一定給了兒子心理慰藉和鼓勵,也是父子相長的一個例子。另外,我們對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時間上相隔20多年的共同興趣也是增進我們父子之情的一個因素。
總之,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既是第一個,也是排名第一的老師。家庭給了孩子自然的基因,也給了孩子品格特質和基本價值觀的“文化基因”。這種“文化基因”既是顯性教喻的結果,更是耳濡目染、潤物無聲的結果。無論孩子到了青少年時期多么逆反,甚至后來的思想觀念、人生態度和人生道路多么反叛家庭,最基本的品格特質最終還是會“回歸”家庭,至少會留下“文化基因”的影子和痕跡,可能是正向意義上的,也可能是反向意義上的。這個“文化”,并非一定與文化程度有關,而是沉淀于文化血脈中的態度。作為孩子的第一任老師,陪伴是父母的第一責任。在陪伴與互動中,讓孩子體驗愛與溫情,讓孩子的好奇與興趣得到激發和鼓勵,讓孩子在引導中形成正確的基本價值觀,既是孩子健康成長的必須,也是父母自身成熟的關鍵。
四川新華電腦學院專業職業規劃師為你提供更多幫助【在線咨詢】